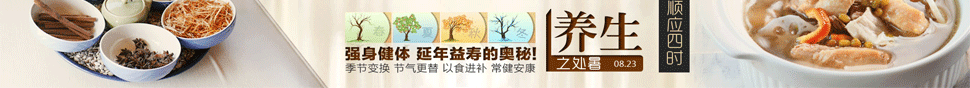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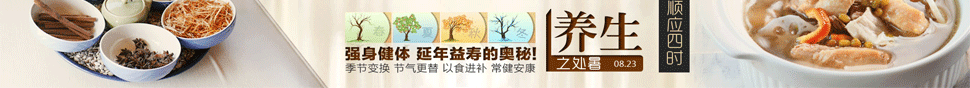
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是明代嘉靖年间吴承恩所著。但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唐、五代时期已广为流传。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夏晚期的壁画中还是唐僧和悟空两人,而元代瓷枕中已出现师徒四人。
二师弟和沙师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也许从本文的主角——驮经图花钱,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民俗花钱取钱币的形制,却并不用于流通,币上内容从花鸟到人物、从仙境到市井、从书法到绘画、从祭祖到游戏、从汉唐到明清、从帝王到平民、从金属到木石……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其纷繁复杂大大超出了当代人的想像。
西游记驮经
更为难得的是,这里所表现的一切,不是站在局外的描摹,而是古人生活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就连我们今天称为“精神安慰”的趋吉避凶,对于当时人也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世界。因此,古人在民俗花钱的设计和铸造上,下足了心思。
西游记驮经
近日新得一枚“西游记花钱”,又称“驮经图花钱”,直径38mm,为中有圆孔的圆形古币。两面皆有栩栩如生的图画,极为精美。
钱币正面为唐僧西天取经归来的情景:悟空牵着白马,唐僧跟随其后,白马驮着经卷箱,箱中光芒四射。
这幅图案多见于元明创制的壁画之上,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并非吴承恩自创。在宋代玄奘取经的故事就被编撰成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时全书的中心人物是三藏法师与猴行者,有沙僧原型深沙神,还没有猪八戒这个人物。直到元末杨景贤编纂的《西游记杂记》中才开始出现唐僧师徒四人。可见此枚“西游记花钱”应是元末之前所制。
钱币背面则为宋代泗州大圣降无支祈图:右侧是泗州大圣站于云端,一手持净瓶,一手指无支祈训斥;左上方是他的弟子方木叉与慧严;左下方则是背压铁棍浸入水中的无支祈。
这里的泗州大圣便是观音的化身,无支祈便是孙悟空的原型。吴承恩是从“禹王降伏无支祈”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将无支祈构画为了孙悟空。在《西游记》第三回龙王说“大禹治水”的文字就充分证明了孙悟空的原形是无支祈。而压在无支祈背上的铁棍便是后来吴承恩笔下的威力无比的金箍棒。
不想这一枚小小的花钱内涵却如此丰富,竟道出了西游记的前世与今身。
民俗花钱的丰富,决定了它的历史价值。民俗花钱在反映人们生活和精神状态时的真实,决定了它在21世纪依然能够具备的亲切感。“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周围装饰一圈元宝,求财求得那么理直气壮、不加掩饰,正是这种直指人心的真实,穿破了时空的阻隔,令古老的艺术品在当下焕发出朝气与活力。
下面再附上老赵对此枚钱币的考证研究,诙谐幽默,有理有据,立意深远,非常精彩!供大家参阅。
花钱研究:必须还原当时社会观念与习俗
作者:老赵
在谈论中,最容易导致无结果、各执一词的,就是不从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时尚流行,审美立场,行为逻辑去推导,而一味立足于图形本身,见一个年轻光头,你说阿难,他说罗汉,你说是康熙他爸,他说是三藏他爹,你说是和尚颂经超度,应是墓葬钱,他说这个和尚是个行脚僧,所以是个护身符,各自都能写出无数理由,又无法说服对方,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咋办?唯一的价值,就是学习到不少广博的知识。
驮经钱
刘源(网名LY)提出,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是明代嘉靖年间吴承恩所著,但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唐、五代时期已广为流传。驮经图花钱主要有两个版式,主要区别在于驮经面一种悟空扛棍,另一种不扛棍。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夏晚期的壁画中还是唐僧和悟空两人,而元代瓷枕中已出现师徒四人,很有见地。
驮经钱存世不在少数,基本形态变化少,钱上左边两人在构图上与观音同处一个云层高度,与下界水波中的猴子不在同一个立场与层次。论具体图形之辨别,理应放置到当时的生活风俗信仰中去做一个体察,然后见微知著,然后去做妥帖的推演。光从图形去论,可能一辈子无定论,你说牵马的,一定是唐僧,我说就不能是慈恩吗?
现在这种钱多了,大家知道“猴子”加“棍子”加“马”加“和尚”的组合图形,在花钱上这么普及,非西游记莫属,其实这个判断就已经运用了当时生活信仰传说的背景作为判断。但是大部分图形的主题与主角,由于时代的久远,加上今人与古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流行要素、审美偏好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解读断层与隔膜,存在了十几代和一百代沟,最关键的,其故事、传说,未必一直如《西游记》一般延续到如今,能继续成为新时代人们的精神点心,所以大部分的主题、典故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主角明星,根本就没这么幸运。他们需要我们去格物致知,去体会洞察。
回到驮经钱,深入一步看,宋元人的信仰民俗生活形态中,他们期盼得到什么?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心灵与现实问题?流行的方式是什么?提炼的模型是什么?社会的旨趣是什么?这些软文化的探索,才能构成当下的我们进入古人生活与生活零件(比如花钱)的钥匙。
我们首先撇开具体图形探索,先说一说宋元时代信仰生活的几个重要要素:一是经市民社会改造过的佛教教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二是观音偶像崇拜与信仰成了百姓生活的重要信仰依托,大量的观音(白衣观音、水月观音)广泛流行,并与生育文化、延命文化挂钩;三是具体的,在崇拜方式中,出现了大量的由庙宇主导的,信徒追随宣扬的,通过口诵,可以避免多样灾难的信仰实践模型(比如口诵观音可避瘟疫、强盗、老虎等灾难的《妙法莲华经》),可以设想,在古代的交通状况和宋代大量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差旅是不可避免的日常活动,从汉代随身携带的保佑长途平安的印章,到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除蛟(祈祷水路平安)、出入安泰(金代钱)、出行大吉(辽代钱,内双系孔)和辽金护身符的发达可见其一斑,在当时普遍观音信仰、当时普遍的信仰需求活动下,本钱未必不包含了这样的一种动机。在此文化背景的体认下,我们来看看这些钱币图形上到底是什么含义。
从已经公布的宋金西夏元期间西游记题材的壁画图形上看,如果足够细心,可以发现其实这么多年取经壁画的主题形式只有一个主要图样。那就是:行者与玄奘步行,前面有水波,空中有观音。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模型想阐述什么意象呢?
1、路途概念。如果本钱表达的主题是已经到达了西天,那么内容中没有对应的意象(如小灵山、堂皇寺庙、如来众佛等象征标志),所以说明取经小组还没到西天,而是在路途之中。
2、遇阻概念。如果是一般行走,起码三藏应该骑马,而徒弟步行,现在这样全队步行,从情理上判断,必然是遇阻。遇见什么阻呢?图中显示得很分明,前有波澜壮阔的大河也,取经小组成员行走在岸边陆地,且已经走到陆地边缘,每个主要图形都显示着有意突显的陡峭岩石。这样显示的目的,就是衬托那条河流的险恶。在下94年去西疆,拜谒玄奘驿站,靠近红其拉甫山口,上有白雪皑皑的7千米的世界第三高峰慕士塔格峰,旁有逶迤巍然的冰川,前面正是一条巨河,河流上的小桥在洪水期被冲垮,波涛湍急,声摄心魄,那时,我想到了含辛茹苦的无奈三藏兄和他的团队。
3、危险概念。这个阻不是一般的阻,因为取经是一个有计划的事情,不但无法从道义上后退,即便从季节上也无法后退,在西北新疆一带,便于行走的季节只有两三个月,到九月,就要下雪,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阴历),届时大雪封路根本无法行走,所以耽搁了时节,后退和前进都有性命之忧。在图中,波浪中有几个孤苦无告的人头逐浪起伏,可见有人不顾危险下河,已经遭受灭顶之灾难。在这种时刻,可怜的以唐僧为核心的取经小组应该怎么办呢!
4、祈求观音概念。自然的条件非人力所能抗衡,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祈求宗教的超自然力量与之抗衡,三藏取经,本就是佛教的开发项目,并且是在观音的亲自挂帅和具体领导下操作实施的,所以,由三藏或悟空,向观音求援,以讨取解决方案,则是再自然顺利不过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取经题材的壁画图形,都表现为三藏与悟空下马礼拜,礼拜的上空就是观音与护法金刚。下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了恭敬,而不仅仅是临水,这个目的与主题已经昭然。
由此反观宋元时期的观音崇拜信仰与旅途的护身的实际需求,用长途跋涉的老祖宗与最典型人物玄奘来做代表,则是最恰当不过了,用玄奘礼拜观音由此最后取得平安与成就,来附会自己生活与旅途的保佑,也从逻辑上是合理的。从宗教角度看,佛教假设需要一个例子来推广当时的主干项目《妙法莲华经》,哪里有比用天衣无缝的玄奘师徒故事更上佳的例子呢?
一则是佛教故事,主题正确;二则妇孺皆知、市井流播,符合传播原则;三则三藏本来就屡屡遇险,本来就该向观音祈求,在故事中没有一次不化险为夷,这样的例子,不正是推广观音法力的不二案例吗?同时,这类图形存世数量众多,延续年份漫长,也在表明用此图形的需求一定很充分、频繁、延续和必要。从花钱这个载体上看,也作如此观。这种类型的花钱也许并不是一个长途的护身符,在壁画花钱上广泛出现这类布局定格的西游记表现形式,也许在当时是公认的最流行的取经大片的海报“POSS”,所以被一再翻版而不另择新图,以免大众误认为其他故事。
声明:
以上部分转自海门日报。原文链接: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hiweia.com/swtz/90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