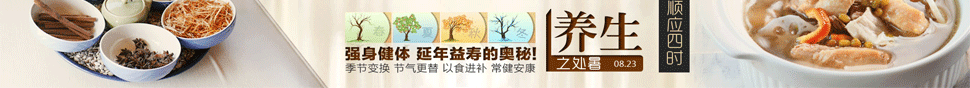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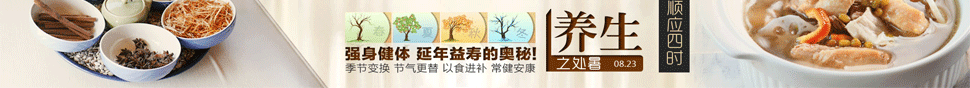
韩育生
著名作家
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甘肃,现居北京。
从小熟悉山野田间花草树木。
在古典诗词中感受万物鲜活灵动,
在美、性灵与感动中寄放现实之外的人生。
著作:《香草美人志》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情怀》、《诗经里的植物》
---------------------------------------------
1.终南路径
刚立秋,西安城里响了一夜雨。“听雨无深眠,睡到云息处”,第二天醒来的感觉便是如此。天气薄阴,往山里去的路上,看到薄雾掩着城郭。
车穿过大峪村,绕着水库,进入了终南山的山口。一浪接着一浪的绿色褶皱和无风孤立的高耸岩面上,苔藓地衣绣出的斑痕山水画一样的痕迹古朴又有活力,一种心神被遮蔽被保护被召唤地俯瞰掷心而来,莽莽群山透出一股终南独有的目光,人如舟叶一般漂移。
传说中的终南山并非都是虚构的说辞。
巨岩扑面,草木如鳞,想到终南正带着自己走向它的深处,心底禁不住起了一阵波澜。习惯性的把眼睛投向绿草的缝隙,坡道灌丛和林下的空地,去寻找绿野中的红黄蓝紫。
不知道这一次,在终南山,自己会遇到多少秦岭独特的花草。花是大自然精灵的呼吸,每一年的花事,是一株草木寻找到自身存在延续最深切的体悟,花间之秘荫蔽着生命之秘,宛如天道循环相继不息的微笑。
问荆,木贼科木贼属
车窗外变换的风景里不时有岩间石屋一晃而过,隐士,求道者,困顿人生路上的迷思者,这些概念从心里跳出。石屋的重启废弃,隐士的静思顿悟。四季在世间,人心也在世间。
吕浩的弟弟用车把我们送到终南山脚去往草堂石子路径岔口的小桥旁。
小桥上,俯身看终南雨后的山溪,跳动在沟壑中的溪水明净闪亮,搅动着安静游离的水草,即使夏日刚过,依旧裹着一股山体深处泄流而出的透骨阴寒。芃芃草木悬在山麓岩壁上,灌丛抓着松石枯枝,偶尔一露的山花在人心里秋千一样荡起。危耸独立的山峰搅合着水流清脆的声音,声音被巨石折返撞击,把人内心的混浊撞的安静下来。人心似被裹着浓雾的莽莽山林捉住,停住,歇住。感觉自己像雨滴一样落向一个崖口,山林静静的肃穆以待,让人捕捉到了终南山“慢”的一点节拍。身子感到了一点冷,这点冷却非秋意带来,而是这山林自带的凉,似被昨日山雨唤醒,一阵阵透过身体,要和城市里面目混浊的人做一个无声又庄重的体息的交换。桥边岩石上晾着一小片翠色的五味子,拿起一粒,放到嘴里。8月终南山的滋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
吕浩带着吉木和我,穿过飘渺雾气,沿着盘旋山道步行去往草堂。雾里似有雨落到头上脸上身上,雨意那么浓,像雨和雾在离别。
山路陡峭,急弯纵横,即使行车,也极为艰难,下山时我们坐着越野车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路是吕浩常走的,他带我们不时沿小径横切。三个闲人在山间慢慢悠悠迂回,被雾惑目驻足,被花草吸引弯腰。
秋花并不多见,在道边,看到了被雨沾湿,一副哀婉姿容的粉红色鹤草,白色如蓬的伞形科植物正是盛花期,花瓣残留的水杨梅不时在路边开成金黄色的小盏。在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地方,低地植被的花期已经进入歇息的阶段,盛开的山花就要往海拔更高的地方才能一睹风采。
从车道拐上山民走出来的小径,感到了一股幽深。小径在雾里蔓延,湿润的凉气呼进气管。古人说终南之肺,中原肺腑。吸引我的到是掩映在草木溪谷里的无声,雾中行走,不时在路边显现一小片一小片禾草蔓长的草甸,村舍门槛上坐着一动不动望着我们的老人。
雨中花草一路相随,雨后半透明的一年蓬,热烈开给世界的大火草(学植物的朋友告诉我大火草又叫野棉花,不知当地人是不是这么叫,我第一次见误以为是某种芍药),黄栌深绿的树叶上,凝满的露珠折射着漫射的光线,好像终南不轻易示人的情绪在一点点聚集。
大火草,毛茛科银莲花属
山道绵延,雾气似有灵又无意,飘渺纠结在身体周围,盛开卷丹在雾中垂在人的头顶,让人有走在内心观想世界的幻觉。
这样的终南路径上,迎来送往过多少路人过客。常住的村民走过这里,为生活艰辛和泥土草木结合,沉淀了西北文化民俗的个性。天南海北的道友为精神的羁绊和寻觅走过这里,灵魂的海洋要把他丢在何方还未可知,但脚下台阶的升降给了攀缘接近的感知。多少琴音颂词被这无声的山路挽留过,推开过,又迎接过。这路像是有淘洗涵养的功能,或者它就是路,以道的形式勾连了世界神秘莫测的变迁。因朋友的机缘,透过草木世界,对自己走在这样的路上,有点点恍惚,好像自己正走在世外的某处。
茅草夹道,走过几棵松杉下的林荫,一片盛开的蹄印橐吾出现在眼前,那叶片的肥美和花事的盛期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路旁一个简易木门开着,进门几步,是一道窄小排木的小桥,正对小桥的土墩上,一棵皮如青桐的青榨槭如风迎接着远客旧朋,桥下水边的泥土旁,几株金黄的宽萼凤仙花开得正盛。
山腹里的草堂,出现在一片山势平缓的坡地上。因为昨日的大雨,吕浩让我倾听背靠草堂的山岩间传来的瀑布的声音。
2.草堂中屋
草堂聚散的中心,就是面南背北的中屋。没问过吕浩草堂的屋舍是否都有特别的名字,走过草堂里错落散布的一屋一舍,那些茅草铺就的屋顶,显出细微裂痕的泥墙,榫卯相接的木屋结构。屋舍尽可能避开了光鲜平整的现代的尺度感(标准化的东西要去做自然可以做到,做到这些并不难。回归到质朴往往要难上很多),一股农耕时代朴素的泥土味扑面,我闻到的是和自己身体里混杂的东西并不一样的味道。这种味道到第二天离开草堂时才让人意识到,曾经凝聚在人心里知识经验的结晶,对于草堂,是被不断消解过滤的东西,那些曾经如百米跑一样竞速过的人生,在这里一步步又重新回归到石头土地的状态。一种自省的安静里,有对生命信仰的另一种重铸。久居终南的人,心里都不缺一枚自然的明剑,或许于外人是神秘,是癫狂,是出世,是自讨苦吃,是难以理解,在他们的起行坐念里则是心中所向的修行。这种超我的实践内化成了信仰的根基,在草堂里生活时,便少了辩驳和相争。“人居欲海以为乐,我居草堂自在行”。虽然深知,这一凡探索更要比世外俗海更加艰险酷烈,并不如表面上所看的那样风轻云淡坐看云起。对于那些散落终南的孤影,待到在岩间使巨石成粉垩,让凶灵化飞鹤,世间便是一个草堂了吧!
终南草堂
雾散后,草堂迎来光,光漏过山崖,漏过林莽,漏下杉木松果的缝隙,透过玻璃窗。我在中屋的地板上走来走去。这个渐渐熟悉起来的氛围里,一份陌生的平静也像一路的雾气一般散去了。面向远山的窗边,一个小瓶里插着一束干枝,干枝突兀如人升腾的意志,又像喷泉的流水。刚进门,和忙碌的包着饺子的大家打招呼时就撇到如日本插花一样摆在瓶子里的枯枝和爬在枝上安静如不动念的蝉影。一种幽静的美感扫过中屋。在慢慢熟悉起来的环境里,看那些挽留了雾与尘的光流动在安静明净的中屋里时,惊讶的发现枯枝蝉由一尺高的枝桠顶部出现在了半尺高的地方。年长的周居士用她台湾腔加苏州话的强调说:“那是活蝉的啊!”活蝉即道,不急不躁。恍然一笑,大概是某位大德在某本经书里说过类似的禅语,击中我心,让那只安静的蝉的倒影出现在我心里。
吃饭时进到和中屋一体的厨房里,厨房窗户半掩半蔽,灶膛里架着柴火,跳动的橘红色的火苗冒着烟,灶火门被火苗烧得黑魆魆的,大锅里,翻滚的水汽弥漫到昏暗的空间里。一股素净的饭香,一股柴草燃烧焦熏的烟熏味,一股勤勉和辛劳凝结的平静的苦味。火苗跳动着,隐逸变动的光和窗户上透过来的光相互交织,朦胧而柔和。这个生活的道场,五谷的道场,多像小时候乡下家中简陋的厨房。
终南草堂的厨房
多少人在这里,安静专注地做出一锅锅的饭,喂得一簇簇蜉蝣的灵魂肃穆起来。
大锅翻滚的开水里第二锅饺子应该熟了,从厨房里退出。光和影中弥散的味道加深了草堂在我心中的印象。
中屋中门没有台阶,为了弥补落差的不便,檐下放了一块落脚的方砖。出屋能看到几丛未开的鸢尾,宽叶憨厚,来年春夏时节,鸢尾花会开的灿烂。几步之外开着一丛萱草,花梗上独存着盛开的一朵,粘着雨露,它的一谢一开和深林四季的一张一合不知是否有人注意过?中屋右手门走下几个台阶,是个简易的洗漱台,到洗漱池边洗碗,永不枯竭的山泉水清凉的冲净了碗筷。几棵乔木正发出它们的新枝,这些叫不上名字来的乔木的枝头,饱满的荚果在风里摇摆。泉水、植物和水上金色的波纹里,透着终南的脉搏。
饭后大家到草堂散步,去看花草,草堂8月的花草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细致的去观察去触摸。橘红色的剪秋萝,挂着水珠的沙参,有广布野豌豆,有紫菀,有小飞蓬,有蓼科、藜科的植物,野草丛中密布了花期刚刚好的川党参,野草上缠着金灯藤,有蝴蝶在花上飞,落在豪放的大蓟的粉色花上,一年蓬肆意的开着,大火草和山下相比到显得零星,刺儿头一般剩了球果的日本续断竟然能长到一人高。靠着中屋的岩边,还看到铁角蕨,小的没人注意,几丛有柄石韦,开成碎金的垂盆草。中屋旁的菜地里,周居士指给我看几棵种下不久的蓝莓,蓝莓果上刚刚凝住一层白霜,遮住的蓝紫色诱人摘下它,品尝它。
剪秋萝,石竹科剪秋萝属
绣球
蝇子草,石竹科蝇子草属石生
在菜地和小道之间一块潮湿的杂草里,一棵野生的兰科植物绶草,把它盘龙一样的细碎小花朝着我的眼睛直递过来。在这个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野外遇到野生兰花的惊喜自然是难以诉说的,更何况在人行的道边遇到这么一朵。我心里的欢喜涌得比周围任何人都激越,如果不注意,这路边的幽微之花,会很容易被当做杂草拔掉。遇到野生兰的盛开,真是忘了修闭口禅。我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份喜悦,并把它和中华文化的德性结合起来做了一点扩展。我不知道兰不开口,它在野地里的秉性和在朝堂上的秉性都一样曲高和寡,幽幽独立。它最不喜别人打扰,它也讨厌自我幽闭于暗室,它自己会在野地里寻找一片湿润的地方,那里有阴凉,通风,必定有恰到好处的光照,周围草木秉性还要平和。它会自己开心的忘我的在那里获得自己生命的证明,证明野地里的兰,是自然生境富饶的象征。离开草堂后,吕浩在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hiweia.com/swtz/8209.html


